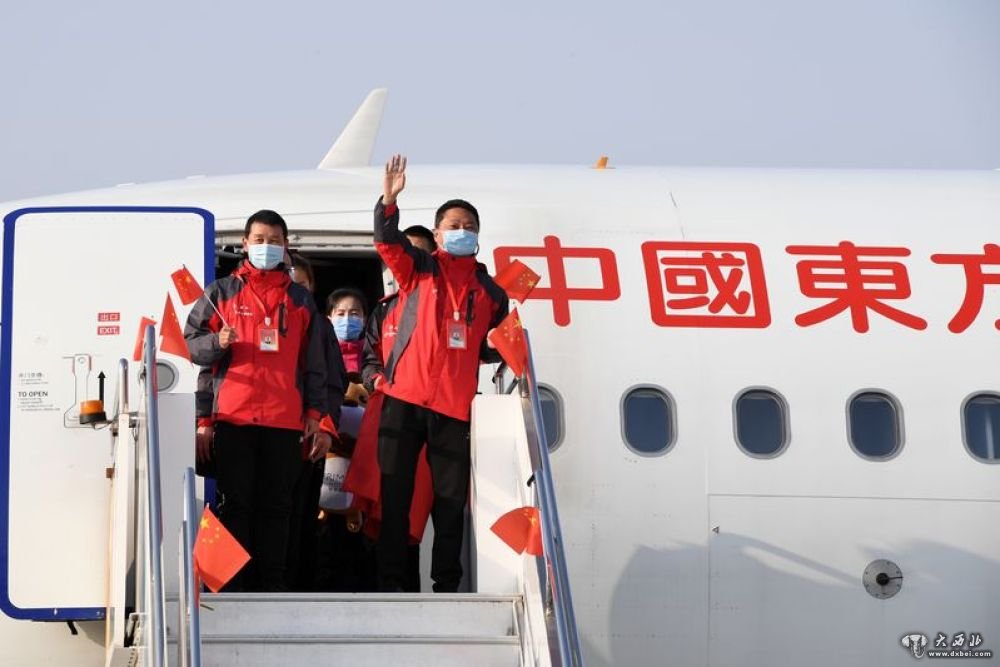果然,十年之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我父亲的希望却在与日俱增;我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简直就像是马上可以看见他手里挥着手帕叫喊:
“喂!菲利普!”
叔叔回国这桩事十拿九稳,大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于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过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都为这件事十分发愁。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年轻人下决心求婚,不再迟疑,完全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到泽西岛去小游一次。
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点,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的。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钟头,就可以到一个邻国去看看这个民族,并且研究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这个岛上的风俗,那里的风俗据说话直率的人说来是十分不好的。
泽西岛的旅行成了我们朝思暮想、时时刻刻盼望、等待的一件事了。
我们终于动身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轮船靠着格朗维尔码头生火待发;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监视着我们的三个包袱搬上船;我的母亲不放心地挽着我那未嫁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我的大姐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一只小鸡一样有点丢魂失魄;在我们后边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使我常常要回过头去看看。
汽笛响了。我们已经上了船,轮船离开了防波堤,在风平浪静,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一样平坦的海上驶向远处。我们看着海岸向后退去,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感到快活而骄傲。
我的父亲高高挺着藏在礼服里面的肚子,这件礼服,家里人在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污迹,此刻在他四周散布着出门日子里必有的汽油味;我一闻到这股气味,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我的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精致的手帕托着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衣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蛎壳就扔在海里。
在行驶着的海船上吃牡蛎,这件文雅的事毫无疑问打动了我父亲的心。他认为这是雅致高级的好派头儿,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两位姐姐身边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位姐姐马上表示赞成。于是我的母亲很不痛快地说:
“我怕伤胃,你买给孩子们吃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她又说:
“至于约瑟夫,他用不着吃了,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我母亲身边,心里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很不公道。我一直望着我的父亲,看见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先前的那两位太太已经走开,我父亲就教给姐姐怎样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一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就立刻把牡蛎的汁水全溅在他的礼服上,于是我听见我的母亲嘟囔着说:
“何苦来!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不过我的父亲突然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他向我们走了回来。他的脸色似乎十分苍白,眼神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我的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