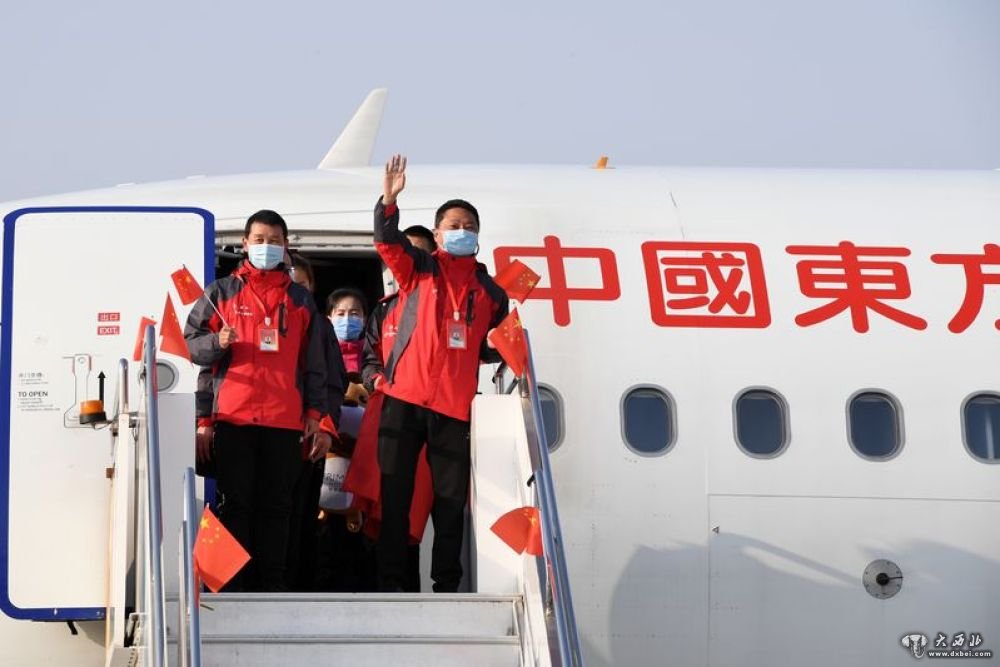摘要:锡伯族是我国北方不断迁徙的少数民族之一,四次历史大迁徙不仅是改写民族历史的壮举,更伴随着锡伯族文化的迁移和改变。200多年后的今天,迁徙的锡伯族与留守东北的锡伯族繁衍发展,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锡伯族文化。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探讨“四次迁徙”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
文化生态学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领域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该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关系,即某一群体所处的环境将对其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环境是指生产模式、居住法则、群体规模等等。斯图尔德认为,“对人们的生存而言,没有于什么比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更为重要”¨J。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在研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文化进化的机制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具体的文化形式是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各种文化只能根据它与环境的关系来评价,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文化之问的差异主要是由特定文化对某一特殊环境的适应过程引起的。越是简单的和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境的影响越是直接。地形、动物群和植物的不同,会使人们使用不同的技术文化和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文化…。
60年代后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帕波特、哈里斯以及沃依达等人,运用生物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概念,提出了修正性的观点:社会、文化和环境都是生态圈的一部分。拉帕波特等人不仅注重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还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以及生态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协调。拉帕波特等人的观点使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更趋于完善。
虽然有人批评文化生态学是变相的环境决定论,但这是片面的。锡伯族四次迁徙所引起的由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引发的民族文化的变异,恰恰印证了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及相互作用过程。
锡伯族系古代鲜卑后裔,依据史书的记载,锡伯族从元朝开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其绝大部分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l636一l648年(顺治五年)编人蒙古八旗,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两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族献给清政府,清政府顾虑锡伯族人居住在一起会生事,难以统治,便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由此开始了锡伯族人民四次历史大迁徙的旅程。
1.进献清朝。1692年科尔沁蒙古的王公、台吉等将所属的锡伯、卦尔察进献给清朝政府,清政府将这部分锡伯族被编人满洲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分别派住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纳(吉林扶余)驻防。
2.南移盛京。由于编人八旗的锡伯族桀骜不驯,独行其是,拒不从命的不安定状态,清政府在1699年至1701年(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间,又将锡伯族主体迁至北京、盛京(今天的沈阳市)以及盛京所属的地区。此次“整顿锡伯旗兵,加强盛京防务”的迁移也造成了祖居黑龙地区锡伯族人口的骤然减少。
3.万里西迁。清乾隆年间,新疆伊犁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沙皇俄国又不断向东扩张。于是,乾隆仿效汉、唐管辖西域的政策,决定移民实边,屯垦戍边,以安定边民的生产生活。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派遣生活在东北,且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锡伯族军卒千余人,连同家眷三千余人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驻防屯田。此次西迁戍边,用时一年零四个月,行程万余里,是锡伯族乃至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壮举。
4.屯垦双城。嘉庆时期,天下太平,加强陪都防务的意义已不复存在。于是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调拨盛京地区的满、蒙八旗去双城垦荒屯田。因为锡伯族没有单独旗佐,是按满、蒙八旗旗丁调拨的,所以当时没有明确记载。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双城地区清查户口时,才把一直计算在蒙古人内的锡伯人填注了一笔J。民族的迁徙引发民族文化的迁移,蒙元时期,锡伯族接受了蒙古文化,使用蒙语蒙文,处于游牧文明时期。纳于清朝统治之后,清政府把锡伯族迁至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纳,后又迁徙到北京、盛京,锡伯族也由游牧文明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文明,并逐渐放弃蒙文蒙语而接受满文满语、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而锡伯族历史上规模大、行程远、路途最艰苦、最令人刻骨铭心的西迁壮举给锡伯族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和全方位的。锡伯族的四次迁移,特别是第三次迁到伊犁河谷的西迁,形成了锡伯族分居西北和东北两地的格局。西北地区主要指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戍边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因为生活在特殊的八旗军营制度里,不能与其他民族随意杂处,加上清政府“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的规定,使其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相对少了一些。所以,长期地保持了自己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东北地区主要指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东北地区的锡伯族,由于居住比较分散,长期与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混居杂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日剧增,因此,汉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分居两个不同地域的锡伯族,虽为同源,但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影响下,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同中有异”的锡伯族传统文化。
1.饮食差异。西北地区的锡伯族地处畜牧业发达的新疆省,加之受到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影响,其饮食以食用羊肉为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莫尔雪克”,锡伯族人把这种菜肴称之为“全羊宴”,汉译为“碗里盛的菜肴”,全是用羊身上的杂碎做的。按锡伯族人的习俗,家里来了贵客,或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主人才会宰羊作全羊席。即用新鲜羊心、羊肝、肺、大肠、小肠、肾、羊舌、羊眼、羊耳、羊肚、羊蹄、羊血、雪青等杂碎做成,每种杂碎做一种带汤的菜,分别盛在16个小瓷碗里,看起来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诱人脾肺。
东北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区,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小麦、谷子等作物。因此,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饮食则以米、面等主食为特色。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稗子面豆包,即由稗子面为皮,红豆沙为馅的主食。稗子颗粒类似小米粒大,色白,产量较低,亩产为300—400斤,是锡伯族很喜爱的一种作物,可熬粥和做成米饭,亦可作煎饼,可发面做豆包。酸茶也是东北地区锡伯族喜爱的由面发酵而成的消暑饮品。用稗子米面或玉米面一斤,黄豆三两,用水泡开,上磨成浆糊状,然后用开水搅拌,放在热炕头上发酵,发酵后就有了酸味,用罗或纱布过淋后,在锅内烧开,放凉后即可饮用,味道酸甜,类似现在的乌梅汤。
2.文体活动差异。锡伯族的先祖,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在清代西迁戍边的生活中,锡伯族营的将士曾使用弓箭这一兵器,多次抗击外来人侵者,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维护安定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因此,西北新疆地区的锡伯族至今仍保留着对射箭运动的执著和热爱,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更有“箭乡”的美誉。“射箭”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特色体育活动特别普及,很多学校都设有自己的射箭队,为我国国家射箭队输送了大量的射箭人才。东北地区的锡伯族由于地域环境已不具备相应的射猎条件,射箭这一传统体育活动也逐渐失去了其生存魅力。但作为射箭雏形的“打瓦”游戏,仍在东北地区的儿童中保留着。打瓦,是一种在辽宁省凤城县锡伯族中很流行的游戏,深受锡伯族儿童喜爱的游戏,原叫“打靶”,由于年深日久,白话为“打瓦”。这种活动源于锡伯族的狩猎时代,是用来锻炼儿童的臂力和眼力的,以使他们成为好猎手。打瓦通常分甲、乙两队,选择在有四五丈平坦的地方,双方各设一块“瓦”,即能立住的长方形石,长约二尺,宽一尺,摆在步量的距离上。有老瓦、后扒、短枪、短线、长枪等多分节的玩法。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特别是地处松花江流域的锡伯族,很多以养鱼为生。清代,松花江两的锡伯族人更是奉令出鳇鱼差,每年为皇帝养殖并运送鳇鱼,供皇帝正月祭祀专用。由此渔猎遗风体现在东北锡伯族的文体活动中。“打螃蟹(kai)”就是由此衍生的东北地区的特色传统体育活动。养鱼的过程中,由于螃蟹对鱼的迫害使锡伯族渔民对螃蟹深恶痛绝。加之,锡伯族人耿直正义对“横行霸道”的人更是恨之入骨。见到螃蟹横行,便用树枝、木棍击打。起初锡伯族渔民将螃蟹放置岸上,几个人是用树枝、木棍强打。演变为文体活动后遂将被打之物冠以“螃蟹”之名,由长约4至5尺,下部约6至7寸,弯度约120度的自然曲棍作为“螃蟹棍”击打。比赛场地不限,通常以道路为场地,先在场地上横画一线为中心线,中线两边3~5丈处,各画一线为双方底线,宽度以路宽为准。比赛分两队,每队3人。先将直径约3寸、高2寸的木螃蟹立于中线上,双方各出1人至中线,于“螃蟹”两边面对站好,用“螃蟹棒”互击三下,而后开打。6名队员于场地相互争打,边打边呵斥“看你再横行”、“叫你横行霸道”,将“螃蟹”打过对方底线记为胜利一次。比赛不论时间长短,最后累计上方胜负次数。运动形式与欧洲的曲棍球很相似。
3.锡伯族语文留存情况差异。史书记载锡伯族很早就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由于从蒙元时期开始,锡伯族就一直受到其他北方民族政权及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的统治。因而,锡伯族语文的发展在保持的前提下,也吸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语文符号。隶属科尔沁蒙古时期,逐渐融合了部分蒙古语词汇,使锡伯语与蒙古语有相近之处。被满族征服后遂改用满语,锡伯族人保留了本民族语言中的部分词汇作借词,但从整体上看,它与满语在声调、基本词汇、词与词的排列次序等方面基本相同。现在满文、满语和它的替代形式锡伯文、锡伯语在东北满族的发源地已行踪难觅,而在新疆查布察尔却得到完整的保存。查布察尔的锡伯族人交流几乎都用锡伯语;各单位的名称、街头路牌、宣传广告等都用“锡汉”双语书写;各级政府制定的各项法令、法规、条例等除用锡伯文、汉方书写外还有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锡汉”双语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在查布察尔随处可见。锡伯语文在新疆能保存下来,首先得益于封闭。锡伯军民西迁后,按兵营制度居住相对集中,很少能与其他人接触。西北边陲又地广人稀,各民族人口聚居地区相隔甚远。特别是锡伯族聚居的伊犁河南岸河谷盆地,南有乌孙山脉成天然屏障,北有伊犁河,相对封闭独立,交通不便,受外来的文化干扰较少。其次,察布查尔大渠开凿成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客观上也减少外界接触。察布查尔大渠因而被锡伯人誉为“母亲渠”、“幸福渠”,1954年成立自治县时,把大渠“察布查尔”作为自治县的名称。再次,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其他民族文化难以渗透。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锡伯族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和佛教。至今,锡伯族的聚居区仍然是自成体系,8个村庄分布在东西长不过三四十公里的狭长地域内。有的村与村只相隔一二里,村内的锡伯族也大多集中居住在一起,这在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另外,锡伯族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教育,锡伯营每个牛录都有私塾,晚清还创办学校,这都为锡伯语文的保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西迁的锡伯族也为西北地区带来了东北的满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已译成满文的各种文艺作品,如《东周列国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据说有些书籍还是皇帝御赐的,这成了锡伯军民西迁后的主要精神食粮。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却在强势的汉语文影响下逐渐淡忘了锡伯语文。现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只有年事较高的锡伯族老人还能记得少量的词汇,如:父亲为“阿谋”、母亲为“额聂”。但是由于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大都是分散而居的,很多词汇的发音出现了差异。例如,黑龙江双城市农丰满族锡伯族镇的锡伯族居民将锡伯族独特的“喜利妈妈”称为“佛头妈妈”,这种称呼更接近满族祭祀的“佛把妈妈”。但辽宁省和新疆查布察尔地区的锡伯族都称“喜利妈妈”。
目前在东北地区已很难能找到会书写锡伯族文字的人。但在仍供奉祖宗盒的锡伯族居民家中,还能看到“锡伯文字”花式的剪纸挂件。4.民族教育差异。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全国唯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的自治县。由于环境相对封闭,锡伯族语言和传统文化风俗保持较好,因此,新疆锡伯族的民族教育以锡伯族语言和文字课程为重点,特别是书面语言教学。新疆锡伯族以“锡汉”双语教学为特色,采用“锡语起步,汉语为主,以锡促汉,锡汉兼通”的双语教学模式,自编实验教材,运用传统的“锡汉”对译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实施“先语后文”的教学程序。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汉化情况严重,传统文化课程的重点则是民族史、民俗文化和民族特色文艺的学习,语言则只要求掌握字母、单词和简单的13常用语。辽宁省锡伯族的民族教育是东北三省的翘楚,沈阳新区兴隆台锡伯族学校从新疆查布察尔聘请优秀的民族教师协助发展锡伯族学校教育。学校目前开设了锡伯族舞蹈、锡伯族乐器、锡伯族语言、锡伯族发展史、民俗文化等课程。锡伯族语文课程在小学一至三年级教学,教材为自编校本教材,内容包括字母、单词和简单的问话。综上所述,锡伯族的四次历史迁徙对锡伯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迁的锡伯族在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东北的锡伯族文化已有很大不同,呈现出鲜明的西北特色和地域性,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整个锡伯族的历史文化,有利于锡伯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罗伯特·F.墨菲.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50.
[2]斯图尔特.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jE: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9—5O.
[3]安镇泰.辽宁锡伯族史话[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8):33.
[4]何永明.锡伯族西迁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J].西北民族研究,200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