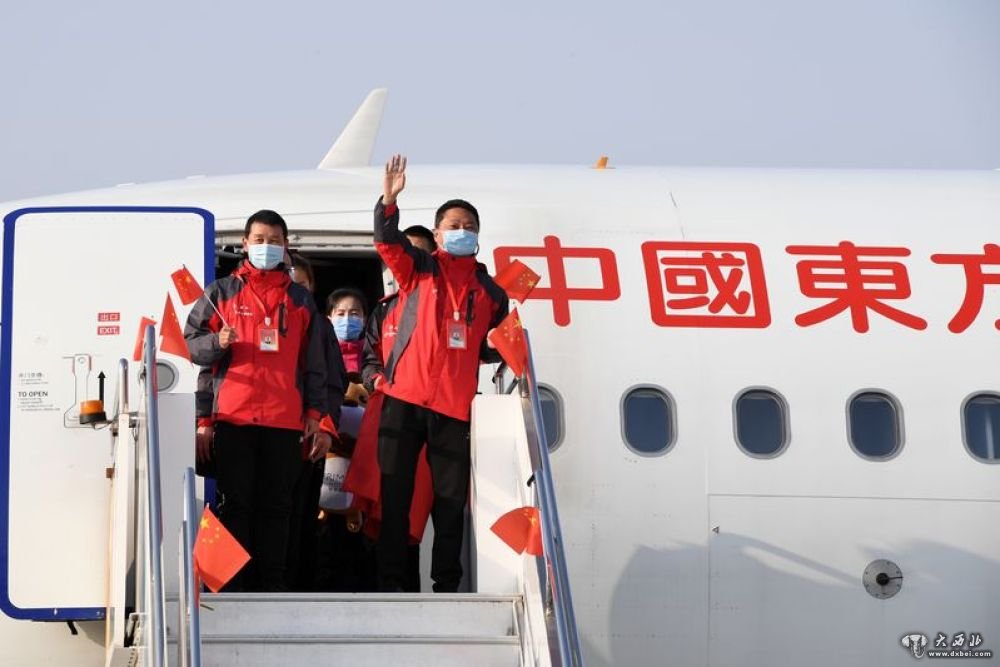他兀地站了起来,惊惶万分:
“什么!……怎么!……这不可能吧!”
于是他们在袍子的皱褶里,大衣的皱褶里,口袋里,到处都搜寻一遍。哪儿也找不到。
他问:
“你拿得稳离开舞会时,项链还戴在身上吗?”
“没错,在部里的衣帽室里,我还摸过它呢。”
“不过,要是丢在街上,我们会听见掉下来的声音的。准是掉在车里了。”
“对,这很可能。你注意过车号吗?”
“没注意。你呢,你也没有留意吧?”
“没有。”
他们相互对视,都变得痴呆了。末了,罗瓦赛尔又把衣服穿上,他说:
“刚才我们步行的那段路,我再去走一遍,看看是否能够找到。”
于是他出去了。她仍旧穿着晚会的服装,连上床去睡的气力都没有了,颓然倒在一张椅子上,既不生火,也毫无主意。
快七点时她丈夫回来了。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又到警察厅和各报馆,请他们悬赏找寻,他还到租小马车的各个车行,总之凡是有一点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她整天都在等候着,面对这可怕的灾难,一直处在惶然若失的状态中。
罗瓦赛尔傍晚才回来,脸庞陷了进去,颜色苍白;他一无所获。他说:
“只好给你的朋友写封信,告诉她你把项链的搭扣弄断了,现在正让人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回旋的时间。”
在他口授下,她写了一封信。
一星期过去了,他们失去了一切希望。
罗瓦赛尔仿佛老了五岁,他最后说:
“该考虑赔偿这件首饰了。”
第二天,他们拿着装项链的那只盒子,按照里面印着的字号,到了那家珠宝店。珠宝商查过账后说:
“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本店卖出的;只有盒子是本店给配的。”
于是他们从这家珠宝店跑到那家珠宝店,凭记忆要找一串一模一样的项链,两个人连愁带急眼看就要病倒。
他们在王宫附近一家店里找到一串钻石项链,看来跟他们寻找的完全一样。项链原价四万法郎。店里答应可以三万六千法郎让给他们。
他们请店商三天之内先不要卖出。他们还谈妥了,要是在二月底前找到原件,店里以三万四千法郎折价收回首饰。
罗瓦赛尔存有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其余的便须去借了。
他向这个借一千法郎,向那个借五百,这儿借五个路易,那儿借三个。他签署借约,同意作足以败家的抵押,和高利贷者以及形形色色放债生利的人打交道。他整个晚年要大受影响,不管能不能偿还,他就冒险签押。对未来的忧患,即将压到身上的赤贫,瞻望到各种物质上的缺乏和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就这样,他怀着惶惶不安,把三万六千法郎放到那个商人的柜台上,取来了那串新项链。
等罗瓦赛尔太太把首饰送还福莱斯蒂埃太太时,这位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对她说:
“你本该早点儿还我,因为我说不定要用得着呢。”
福莱斯蒂埃太太没有打开盒子,她的朋友害怕的正是这个。要是她发觉掉换了一件,她会怎么想?她会怎么说?不会把她看成偷窃吗?
罗瓦赛尔太太尝到了穷人那种可怕的生活。然而她勇气十足地横下了一条心。必须还清这笔骇人的债。她一定要还清。家里辞退了女仆,换了房子,租了一间屋顶下面的阁楼。
家庭里的粗活,厨下腻人的活计,她都尝遍了。碗碟锅盆都得自己洗刷,她粉红的指甲在油污的盆盆盖盖和锅子底儿上磕磕碰碰磨坏了。脏衣服、衬衫、抹布,也得自己搓洗,在绳上晾干;每天清早她把垃圾搬到楼下,送到街上,还要提水上楼,每一层都得停下来喘喘气。
她穿着同下层妇女一样,挎着篮子上水果店、杂货店、猪肉店,讨价还价,挨骂受气,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保护她那一点儿可怜巴巴的钱。
每月都要偿付几笔债券,其余的则要续期,延长时间。
丈夫每天傍晚要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夜里常常干五个铜子一页的抄写活儿。
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年。
十年之后,他们一切都还清了,不但高利贷的利息,连利滚利的利息也全都还清了。 (责任编辑:鑫报)